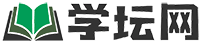心歌一曲唱壶口
2021-10-19 05:19:46 29
我是秦晋山水中的匆匆过客,我是黄河之神的信徒,我从江南绵绵烟雨中走来,走进“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
中华帝国的西北山水我并不陌生,我记忆的相册里,一帧又一帧的大漠孤烟、飞沙走石的相片,恢弘、苍凉、浸入骨髓的冷峻,让我向往着壶口瀑布对我灵魂的洗礼。七年前的夏天,我打马天涯,独行西藏,把自己交付给远山远水的沉静、明丽和苍茫,我觉得自己本该是茫茫草原的儿子,是雪域高原臣民,但面对温驯的黄河源,我有些失落。站在青藏高原的阳光里,我的脚下是黄河源流的清澈河水,纯净、纤柔,甚至孱弱。水过卵石,闪出一丝涟漪,一圈、又一圈,似华尔兹的舞步,围着青茎打转……这是我梦中的黄河么?这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黄河么?黄河的诗章不应该这般婉约,黄河的心声不应该是宛如箫歌笙唱的轻歌曼舞!
我面朝东方极目远望,湛蓝色的天空下,天高地远,那是黄河孕育生灵的方向,那里有黄河长歌当哭的回响,那里有万里江流一峡收,一里壶口十里雷的磅礴,那里有唐诗宋词的飞韵,有穿越古今的狂放不羁,有黄河向往的海洋的辽阔。我敬重我脚下的涓涓溪流了,它是黄河的母亲,或是黄河的儿子,母亲用乳汁孕育了黄河,儿子用忠诚的流向和永不歇脚的流程,成就了黄河的博大。
在我的憧憬中,壶口是豪气万丈的,豪雨中,长风里,或者阳光饱和、飞雪漫卷,壶口都有它独有的风姿。秋高气爽中的壶口是朝天而歌的一管小号,风高雪密中的壶口是临风嘶鸣的战马,而萧瑟秋风、温婉秋雨里的壶口飞流,一如汗津津的歌手在摇滚着一腔澎湃的激情,浩浩荡荡、摧枯拉朽是我所膜拜的气韵……所以,我更钟情风霜雨雪厮守的壶口——雨,是壶口忧患的泪水,风,是壶口深邃的鼻息,是壶口临风而舞的长须。乱雪飞渡中的壶口,是屈原拷问苍天的《天问》,是将士驰骋疆场的一柄长剑,是炎帝手中的一壶老酒。黄河的灵魂是涣涣之水,壶口的生命因水而生!
恰好,眼下的秦晋大地秋雨绵绵,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黄土气息,虽然没有含情脉脉的秋阳,没有鹧鸪声声的呢喃,但这是一个亲历壶口瀑布的绝好时节,淅淅沥沥的秋雨在风中横走斜插,滋润着我对黄河、对壶口瀑布经年不息的向往。上苍、秦晋大地厚待了我的朝拜。
走出酒店的大门,壶口瀑布的吼声便踏歌而来。这是大自然的绝响,是只有壶口才有的唱响长空的心音,是黄河带有母性的呼唤,是光未然笔下铮铮铁骨般的文字里马啸声,是洗星海的旋律中的歌喉,是跳荡在中华大地之琴盘上的音符,是黄土高原掷地有声的信天游。未曾谋面声先至,长歌当酒迎客来,这是壶口瀑布的粗狂,是西北汉子的豪爽。
两岸峭壁夹持,红叶漫卷,壶口似豪情万丈的诗人,不管不顾地唱着黄河的赞歌。走近壶口,脚下似乎在颤栗,大地在沉沦,黄漫漫的水汽恰似云蒸霞蔚,遮天蔽日,在目光的尽头拉起了一幕不可洞穿的雾帐,你看不清壶口之上的黄河,究竟是温婉的仕女,还是蓄势待发的战士,仿佛这威武不屈的灿烂之河,就是从天而落的水神。面对黄河、黄河壶口的浩然之气,旅者、歌者,暂且没有了世俗的杂念,人生杂怀、苟且之念,人性倾轧的困顿、灵魂的厮杀的血腥,在壶口瀑布飞流直下、劲水穿空的恢弘中荡然无存。这是黄河伟大之所在,是壶口瀑布的魅力。
如果说黄河是皓首仰啸的诗人,壶口就是黄河手中的一本百读不厌的诗书。湿漉漉的岩石如质地坚挺的诗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这是地质之神赐予黄河的诗行么?这是比《诗经》还要古老、沧桑的诗章啊!岩石平整、光滑,清晰的纹理一如竹简铺排开来,赤褐色如浓墨泼过,似有线装书流淌的墨香。岩石延至河心,毅然决然地嘎然而止,如诗仙李白在起承转合之际断然收笔,留下黄河大剧的悬疑,留下了国画的留白。黄河把诗眼、把雷霆之声的韵脚留给了天涯旅人,留给了黄河的香客。黄河的壶口瀑布像一个满腹经纶的智者,匆匆步履者何以能读懂她心中的锦囊,黄河经年不息的咆哮中,能否唤醒人生过客瞻前顾后的旅痕?
涌来万岛排空势,卷作千雷震地声。壶口的大气磅礴让你血脉贲张,让你觉着人的渺小,甚至让你仓惶、惊憷,但黄河是宗教,是老祖母的肺叶,是母亲的胎盘,黄河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气势,黄河、黄河壶口是干净的、纯粹的,干净得只剩下黄涣涣的流水,纯粹得只剩下永不歇息的奔跑——黄河的脚下没有驿站,壶口的精神里没有懈怠。黄之灿然,是中华民族的肤色,是华夏始祖高贵的胎记;泱泱之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气节。
铁马冰河,天地苍茫,黄河之水天上来,来的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乡愁,是扯也扯不断的三千尺的绵绵不断的怀想。壶口见证了历史,它是历史岩层中的一页化石。两魏金戈铁马的厮杀,抗日将士几渡壶口的惨烈,都是黄河之水打湿不了的记忆。也许,壶口这截历史的记忆片段,就这样随着马帮的脚印和铃声,散落在冰川雪野和吉县城的老街老巷了,那一面烟熏火烤的老墙上也许还残留着马锅头的酒香、烟草与咕噜咕噜大口畅饮的粗茶的味道,这味道中甚至有皮领褂和马粪混合的气息,但黄河、黄河壶口瀑布,却永远是鲜活的,壶口就像浴火的铭文镂被刻在山陕大地的骨血之中。
很遗憾,我没见过冬日时节的壶口,想必是雪压青石、冰封壶口,而壶口定是如安详入睡的圣母,冰心玉洁的她,安卧在秦晋大地的怀抱,冰凌是她发际的玉簪,她的头颅枕在宽厚的黄塬之上……三三两两苍鹰飞过,遥看陕北的血性汉子为黄河壶口而起得腰鼓,连那株红艳艳的山丹丹也不忍打搅壶口的春梦,将绽放的声音交由黄土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