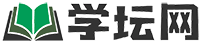母亲的树
2022-03-11 22:51:02 12
在我家乡的小院子里,有一个梨树比我的小九岁。梨树在年轻的春天一朵年轻白花悄然开花,然后落在英语中,绿色油的果实悄然生长。十多年来,我经历了相对的死亡,小庭院是荒谬的,梨树没有丝毫和衰老,就像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年一年,把鲜花和水果放在树枝上。那是母亲的母亲。

母亲的生命非常短,只活到三十年。然而,由于自己的短暂而忽视了生活并没有被忽视。在第一个二十九年的寿命短期下,母亲几乎经历了六年或十七年出生的普通人的艰辛,所以她将去三十岁的年龄,长途渴望和完全遗憾。
我的祖父是一个脱衣服的浪费。当你四十岁时,他拿了一个盲人从外国寻求一顿饭。一年后他有一个母亲。聆听母亲说,虽然奶奶是眼睛,她看起来很善良,温柔,她的身体也很苗条,村里的女性是不同的。但是祖母只为她的祖父生了一个孩子。母亲是一个女孩,不符合农村人民的健康概念。
在祖父的责骂和殴打中,母亲生长到十一点。祖母在那年死了。母亲说,祖母曾非常初前过肝病,最后发展成为肝癌。有无数的夜晚,祖母的肝脏疾病,在床上管道,母亲抱着祖母的身体。其中一个疾病通过了,祖母把母亲放在他的怀抱中,叫她的小名字,匆匆,我去世了,我打算这样做。母亲不禁哭泣。
祖母在乡镇卫生中心死亡。这是四十年前的一个冬天,冬天比现在更冷。祖母生病了奶油。每当疾病时,我忍不住在床的墙壁上踢它,我有一个钝的环。仿佛踢了这四墙的绑定,你可以进入一个无痛的世界。多年来,我的母亲站在祖母的祝福面前,泪水和恐惧敬畏她整个童年。
祖母的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在乡镇卫生中心度过。母亲每天都回家了,为奶奶给了祖母。她穿着奶奶粗糙的棉裤子,忍受了孩子的笑声和寒风的吹口哨,然后去山路到乡镇。母亲说,曾经,也就是说,她最后一次受到惊吓,她非常统计,她非常统计,乡镇的人将成为。这是我最后一次给祖母,我的母亲拥抱旧棉质夹克的米饭碗穿过健康中心的花园,然后搬到了母亲的病房。她非常焦虑,不关注脚。她说,只担心寒冷,否则她肯定会绕过埋藏“炸弹”的松土。这种土壤“炸弹”用来炒野猫,狗的蟑螂,当时很常见。母亲说,在炒后她才感到惊讶,并没有生气。然而,保健中心的一部分冲过来,看到她没有受伤,我为自己嘲笑。这笑太苛刻了,所以母亲从事哭泣,然后诅咒现场的每个人。母亲一直尴尬,那些人已经回到了房子并关闭了门。这是祖母的名字,让这个孩子和成年人之间冷静下来的争端。母亲第一次听到病人的声音,从祖母的牙齿上撕裂了四分五尺寸的声音,在病房墙上有一个沉闷的直言不讳。她哭了,跑了,她哭了,跑去打电话给医生。医生只会使用一个“生病的药”,现在我想来,应该是一个克拉德的代理商“du ke”。之后,在“药物药物”之后,奶奶没有醒来,她进入了一个无痛的世界。
母亲没有上学,她回到了家庭农民从三年级的课堂休息,直到20岁20岁,母亲娶了房东的父亲。母亲的想法是一个如此贫穷的家,也带来了一位老年人,家人嫁给了条件,我担心我总是生气,我只能嫁给“小房东”,谁不敢说消息。但母亲错了。父亲脾气暴躁而不是很无言以来说,他从未照顾过母亲的母性。在睡眠的日子里,他从未怀孕过一个美丽一个家庭的情况。我正在战斗,打人,是他常用的艰辛方式。母亲经常和姐姐说,她的生命并不好。
父亲的死是一个意外。村里的人赶到了邻近的村庄,有一场战斗,他独自死亡。母亲哭了说,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生命。我父亲的死让我和我的妹妹发现这个家庭实际上被她父亲支持。
母亲没有再婚,她已经认可了。她说,她在这一生中只用姐姐养了我的成年人,她愿意在那一刻死。我当时没有完成我的母亲。,我一直以母亲对我和我姐姐的深深理解它。现在,用言语渗透是非常绝望的。
那时,我们的三个必须忍受很多,忍受这个家庭没有人,忍受沉重的活着,外面的眼睛......这是肩膀薄的肩膀。在我的想象中,我和我的妹妹坐在一个篮子里,被母亲在生活方式上捡到了。我一直担心我的母亲仍然可以走远,她太累了。
袁澍在几年后。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他来自哪里。从过去两年中,他似乎从那天陪伴在母亲面前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母亲经历过什么,她接受了袁澍。没有葡萄酒,没有仪式,但是我们家里有一个男人。
我经常比较袁守和父亲。结论是她比父亲年长,而不是父亲。对于之前的一点来说,它实际上是不成时的,因为我们在几年前将袁舒的父亲比较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袁澍非常爱我的母亲,爱我和我的妹妹。母亲已经完成了领带,曾经,袁澍主动说母亲没有解决,还有两个孩子。我看到母亲的眼睛红色。后来我想,我的母亲肯定希望在袁澍的肩膀上发誓。但在第一年,母亲和袁澍的相处一直非常平坦。
母亲贫血的第二年突然变得非常严重。在县里去了几家医院,我吃了一些药物吃,当我很好时,我总是很糟糕,经常晕倒。那一年,袁澍种了一个梨树在院子里。他说这是母亲,梨树正在开花,母亲的疾病很好。我正在浇水梨树,期待着它。但是那年梨树没有盛开,我只发了很多分支机构。我对姐姐非常失望。袁淑说,等待明年,它将明年打开树的花朵。
袁淑素基督教。那时,似乎我仍然不必相信自由,所以这是秘密的,我原本不知道。后来,我的母亲也相信它,袁淑让她坚信普遍的主人会带走她的疾病。他们祈祷这看起来很尴尬,让我相信将有一个普遍的大师,在屋顶上微笑着看着这个。我们都期待着主看看像观音菩萨这样的精神。
虽然主终于未能看到圣灵,但母亲仍然在她的过去两年中,她的生活经历了很多幸福和浪漫的从来没有。我为母亲和元蜀举办了西方婚礼。那是经过重视母亲的母亲,袁舒把她弄起来,在门里有一个团队迎接新团队。袁淑突然说,我们还没有成为专业人士。母亲很惊讶,是不是要采取婚姻证明吗?袁淑说,那不是,没有仪式。现在我会给你发誓。所以元舒称我,给了他和母亲的婚礼。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会问袁澍和母亲袁澍和母亲问道。我问道,袁淑,你愿意嫁给我的母亲吗?无论是贫穷,疾病......我问,妈妈,你愿意结婚袁舒吗?无论……
现在我想到了元澍的庄严表达和母亲的脸是红色的,我意识到在过去两年的母亲的生命中,她渴望拥有一个漫长而几乎绝望的幸福。虽然她生病了,但她一天后晕倒了,她的幸福仍然是真实和触摸。
母亲去了第二年的春天。梨真的很开放,我不能说话,但一棵小树,树枝饱满,尘埃是白色的。那天晚上,我看起来像个月,我起床,小便,我看到袁澍来看梨树。刷子的尿布非常清脆,我说,我在晚上看不到它,当我明天刚出时,我会看看它。如果母亲的声音很好,她说,孩子不明白,进去和睡觉。
第二天,在阳光下出来之前,我看到了白色花瓣上的红色阳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没有好看昨晚在月亮匆忙。我跑来问袁舒,袁蜀实际上坐在床边。母亲离开了。梨是开放的,但母亲仍然消失了。
在梨树下拍摄十几梨,它一直是绿油。我将不愿意和姐姐一起吃饭。我们知道这是一位母亲。我们把它带到了母亲的坟墓里。袁淑静看着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他静静地之后,我带着我的妹妹。
我总是认为元澍从天而降,时间带来了他,给了母亲两年的幸福,帮助母亲带来大,然后把他带走。我们还没有来偿还他。只有那种梨树一直在留下来,分支落下,青年是无穷无尽的。那是母亲的母亲。这是生命,爱,浪漫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