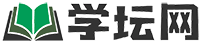归期
2021-01-29 19:53:29 48
30年后,该平台将是空的。风吹雪,黄沙旋转,悬挂的停车牌像骨质疏松症一样嘎嘎作响。在警笛声中,我转过头来,他们会像往常一样出去,然后涌向平台的尽头。我将凝视着他们,他们的笑脸颠倒过来,他们的脸冷得发红,他们的脸像蓝天和白云被车票所反射。我将走向烟熏烟熏烟熏小门的检票口,将自己沉浸在拿着苹果手机的寂寞人群中,并再次使自己相信他们有机会获胜。那时它们将随风消散,而中国的最后一辆绿色火车将随风消散。那时,与过去不相容的现在将风起云涌。我将独自一人,走向检票口并持之以恒。大风大雪。

检票员俯身检查我交出的票。 “姐姐,你自己吗?”我听到他说:“从南方听重音吗?”
“嘿。”我说。 “一家人住在南部,你必须回家看看。老房子需要拆除。”
“每个人都必须被拆除。”他说。那一刻,我闻到了烟味。突然有东西从我的头顶压了下来,我抬起头,看着一系列烟圈争先恐后地串成一串,静静地飘向红色的天空。就像星星一样,灯光在颤抖,短途汽车拿着一个广告牌,正方形和正方形,在黄色背景上带有红色字母,昏昏欲睡的眼睛和棉cotton一起下垂。他摇摇晃晃地走来,张开嘴,嘴唇上下裂开,白烟的顶圈散开,远处传来鞭炮声。我走了两步,然后回头看,他们很高兴,他们精疲力尽,他们像长城一样握着他们的手,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春风,海浪接here而至。我握着母亲的手跳来跳去,我拖着手提箱,ing着跳,我闭上了眼睛,再次睁开了眼睛。司机仍然张开双臂站在我的面前,我们在寒冷的风中颤抖。
“给张武。”我说。
彰武色彩缤纷后,彰武百花齐放,彰武曾经发出了四面八方不容忽视的光芒。尽管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风在这里咆哮,尽管内蒙古的细沙总是堆积在路面上,即使白杨树在蓝天下呈灰色,弯曲的砖瓦房像干草堆一样散落,至今已经有40年了。梦想,安全的避风港,乌托邦像旋风一样闪烁。在车上,我想到了上学的日子。在我的办公桌前,我以为我会在20或30年后乘坐短途巴士返回张武。我想起了上学的日子。那时,我正忙于写作,亚热带的黄昏来了。 ,暮色就像成千上万的书签直接指向牙齿之间。我出生于辽宁,三岁时和家人搬到浙江。除了对长辈的生动描述,以及回家的几段短途旅行之外,我无法理解北国。但是后来我想到了。数学问题和凝视使我头晕目眩。那时,我想到了低矮的草绿色建筑,一排排灌木丛,泥泞的墙壁上凌乱的电话号码,以及我的祖母缓慢地起步并擦去了塑料。在桌布上铺沙。他们叮当响了眼镜,抓住了熏制的猪蹄,打开门,对我微笑,对着我晃来晃去,像是一盏灯。那时我并没有被回忆所淹没,我充满了想象力,然后我想到了自己一个人走进房间,脱下围巾,爷爷立刻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睛闪闪发光,两条腿从床的边缘。当时我在想,不知不觉地哭了。
驾驶员座位上咳嗽了。整辆车倒挂了一会儿,车顶像大雨一样猛撞在车前草上。我看着窗外,突然变得烦恼。我在颠簸时大喊,叫他停下车。 “你怎么了?你留下了什么吗?”他按自己的做法问,但“不”,我苦涩地皱了皱眉,“你在哪里开车?在阜新市?我要去-”
“不是彰武吗?”他说,点着烟,似乎有点骄傲和遗憾,并指着一座摩天大楼,“它已经很久以前改变了。您回到这里已有多少年了?一种风格使它变得更早了吗? ”
汽车又开了。我停下了。三十年前,我的想像力很丰富,肩膀上的记忆像羽毛一样轻盈。三十年前,未来就像东北平原一样广阔。我实际上在三十年前就想到了这一切。我看到纸牌逐渐卷曲并变成黄色,然后从我的手指上消失了。我看到我的后背迅速弯曲,皱纹被弄平了,孕妇旁边的孩子们变成了成年人。我对绣花枕头感到恐惧,不是因为漆黑的夜晚,而是因为漆黑的夜晚一定会变成白日,流水会冻结成冰,而我当时所在的房间最终会变成几尘埃。尽管我们不会谈论它,但是不同的过程将导致相同的结果。每个人都有预测的能力。 30年前,我在走廊的入口处停了一会儿,转过头看着我-一位46岁的瘦女人-从钱包里掏出40元钱交给了短途旅行司机。
此刻,我抬头望着四层楼的建筑。走廊入口处的木门已腐烂一半,“申请证书”或“修理下水道”字样已经模糊。拆除办公室主任听到了声音。施工现场的方向充满噪音。 “你会在五分钟内到那里吗?好吧。”我对指甲大小的手机说。 “我在楼下等你。”
我与导演握手,打招呼后,两个人一起上楼。当穿过吱吱作响的木门时,我想到了友谊,道德判断,朴金慧,秘密爱情和三维几何。我已经走了十多次,既累又快乐,既对即将来临的会议感到兴奋,又对几天后的一次间隔感到沮丧。那时,我充满了奇怪而奇怪的想法。那时,我充满了向往,常常陷入美丽的梦中。拆除办公室的主任走到我旁边,我拿出了钥匙。 “你的第二个女儿要参加高考吗?”我听见他隐约地问。我回答,“是的,她数学不好。”
房间是黑暗和凌乱的。我走进去,奶奶打招呼,跪下来找我拖鞋。当我走进去时,走廊是空的。在我身后的姚主任问我是否应该换鞋套。我知道这是客气的话,地面上满是沙子,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清洗过。我再次说:“你和我奶奶同姓。” “这是一个巧合,”他随随便便地说,“您上次说的是补偿计划-”但是我没有听他的话。我环顾四周,滴着观音的花盆不见了。缺少带有“ Shou”的挂历。装有各种瓜,水果和鱼的小冰箱不见了。我奶奶过去常常从那里找我饮料。我祖父亲自制作的长桌子已经不见了,他喜欢生病前做木工工作。锅碗瓢盆无处不在。在炉子上,洗衣机前面的架子上有硬毛巾。当时,我的祖母站在我旁边,拿着蓝色的星星背景,等着我洗脸。擦拭我……“嘿,我几岁了,小时候请问我在哪里?”她起眼睛,微笑着,“你只有三岁,你几岁了……”当把我和我的母亲送回南方时,爷爷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突然指着盆花,告诉我他如何设法喂了它...但是盆栽的花不见了。他们温暖的香气仍然弥漫在房间里。但是盆花不见了。
导演再次说:“在城市给你盖房子,没关系。”我在房间里四处游荡,他一直站在镜子旁边,“补偿……看,还高一点,你也不住在这里。”我听见了,就在我老祖母卧室的门口,转过身说:“我不认为十万左右太多了。”他抽了烟,摇了摇头,然后我跟着他。他补充说:“补偿是合理的,您很乐意将其拆除,但您说的很多……”此时,我瞥了一眼房间,忘了我以前做过的腹透,床还在那里。
我走进了房子。奶奶坐在低矮的凳子上,鞋底。在对面的茶几上,电视上播放着家庭伦理剧。爷爷躺在粉红色的床单上,侧身转身,戴着老花镜,拿着我给他的《中国国家地理》。桌子上有一对雕塑。老人和老太太坐在摇椅上,一个正在看报纸,另一个正在编织一件毛衣。扑克牌散落在方形桌子上,桌子的侧面有三把椅子。我们曾经坐在那里玩“四一四”,然后他们以混乱的方式砸碎了桌上的大牌。我走进了房子。拆除办公室的主任在等待我的答复,但我急于找到奶奶的珠宝盒,毛主席给奶奶的报价以及奶奶覆盖着纱布的电话。上高中时,我呆在学校,每周回家一次。每次我打电话给他们时,他们俩都赶着去接他们。挂断电话后,我曾经偷偷哭泣。但是现在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像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你是对的。你弄清楚了,随便你做什么,”我心不在a地说道。 “-但是三万太少了。”我看到北方寒冷的冬天的阳光透过不再存在的窗帘照耀着。我看到自己三十年前站在同一位置,浑身发抖,看着床单和床垫消失在看不见的地方,露出了床的丑陋框架。他们总是在这里等我突然想起的地方等着电话,然后等着我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从广vast的浙江回家。这是我的家,辽宁是我的家。这些年来,我改变了口音和习惯。我在南部学习,工作,结婚并育有孩子,但在梦中,我总是站在雪地上,手里拿着老赵头勋。鸡。这是我的家,我永远不想离开。
姚主任看着我。他耸了耸肩,屏住呼吸,大步走向门。 “那么我们都退后一步,你能成功吗?你也是一个明智的人。”
“那么七万。再加上你答应的那套房。”我毫不怀疑地说。他看上去很不高兴,但勉强地点了点头。我们握手,站了一段时间,然后走了出去。叹了口气,我锁上了门。
我上楼了。我转动钥匙,推开已经粘贴的铁门,并将其撕裂。房间像春天一样温暖,橱柜里装满了小食物。奶奶向我打招呼,而我的祖父下床向我打招呼。他们把我最喜欢的零食包装成袋。我站在那儿,对着镜子看着我,我像一个矮小的冬瓜,我有一个蘑菇头,我比他们高一点,并且我有皱纹。我从这扇门走进去,又走了出去,我大声喊着“我回来了”和“再见”,来回交替,从未停止。爷爷站在门口,奶奶站在风雪中,默默地看着我们。
“上大学时,你会自己一个人来的……”奶奶喃喃自语,好像我已经忘记了:“现在飞机快了。你不怕它。奶奶会付车费的……”
当我上车时,我听到他们喊着,要求我明年再来,“一定会再来。”他们穿着军大衣,只露出眼睛,在飞雪中站着不动。寒风使我的眼睛受伤,所以我滚下窗户,向他们招手。
我向后退了两步,看着天花板,地板和废弃的木床。这就是我们一生中实现的一切。姚导演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门口,不耐烦地看着我。这时我转过头来。
“别开它……请,任何钱都可以。”我说。他有一个直的后背,也不允许喙,就像是我脸上细线延伸的罪魁祸首一样,铁路小学的罪魁祸首被风和沙子淹没。我的声音微弱,我的腿在颤抖,我从未如此无助,但我看着他。 “我会给你尽可能多的钱……请……不要拆毁我的房子。”
当然,他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