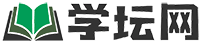“西伯利亚”流放记
2021-01-05 01:23:42 45
除了凉风的沙沙声,教室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寂静的。

早晨的景色仍然出现在我眼前。
袁老师交错地走进教室,在教室的角落里像是阅兵般的将军。他轻松地抬起量尺,随时准备“举起刀子并落下”。他高大的身材高大挺拔,像雪松树。老师的形象威严,但我认为老师很幽默。他的四川话甚至让我大笑:我看到我的脸上充满了肉色,嬉皮的笑容,眼睛eyes成只有几毫米的空隙,露出了嘴巴,露出了黄色的牙齿。我的笑容更加夸张,尖刻,有些娘娘腔。
我的这种形象引起了我的责备与愤怒,但我感到非常自豪。
袁老师用锐利的眼神凝视着我,用烟熏烟熏的黄色手指指着我,用那双旧眼睛凝视着我,在课间停顿了2分钟,但我仍然视而不见,什么也没听到。
“易汉瑞,站在后面!”袁老师一直坚持到最后,像火山一样爆发。他坚决地把我的座位调到最后。从那时起,我住在这个遥远的“国家”。我的心极难过,我会像苏屋一样,远离“中心”而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为什么我的命运如此悲惨?
我很沮丧,我只是觉得袁老师抛弃了我。
但是,第二天,老师仍然举起我的手,关切地有意义地对我说:“消除你的不良习惯,袁老师仍然对你感到乐观。”这时,我的心不再落在西伯利亚。僵硬。
北方的风在吹。从那时起,每当老师在数学课上给我一个好样的表情时,我心中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暖流,因为我真的感觉到袁老师的好意,严忠友很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