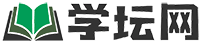面具中的罪恶
2020-10-26 21:56:00 57
我认为我有罪,就是我照镜子的时候。显然,没有面具,我是乌托邦的儿子,他恐惧而怯co,痴呆且躁狂,动荡而安静。这真糟糕。每个人,也就是被蒙面的人,都谴责并压制掩盖下的所谓邪恶。他们声称那些显示自己的自由和自我的人是暴徒。自然,我每周准备七天的口罩,以掩盖新生儿应受责备的真正罪过。

我住在内城的一个租户区。走廊凌乱,墙壁上满是绿色的头发和精神病患者的涂鸦。据说精神病患者在死亡之前不戴口罩,这引起了当今魅力四射的社会的恐慌。每个人创造的当今社会是这样的:稳定,和谐,遵守惯例以及充满向往的夸张笑脸面具。他们将统一的笑脸描述为满足,将裸露的脸描述为恐怖和忧郁。
每天早晨,只要戴上口罩,我都会收拾行李去上班。乘坐地铁的两名年轻妇女正在政府面前热情地讨论着花坛。他们微笑着称赞花朵和植物像颂歌。他们很有礼貌,互相称赞。他们说市长的头像用水洗的鹅卵石一样光滑,并且说他们讨厌所谓的暴徒和精神病患者的游行。幸运的是,他们从未获胜。尽管我的胃里有泛酸,但我还是坐直了身体,并调整了口罩。老实说,昨晚我看到暴徒和精神病患者的游行队伍。但是,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每个不同的面孔。他们举起手,仿佛眼前有生命的漩涡,到处都是巨大的波浪,这些波浪并不重要。
但是,我不敢再看它了,因为我拥有公认的社会地位和至少体面的工作。我应该每天工作到深夜。我笑着接受,并告诉老板这符合我的生活。在面具下,我痛苦地喃喃地说了几句诅咒。我受不了他指定的镜架和他给我的口罩来束缚我狂躁的血红色心脏。
而且深夜很危险。空气中弥漫着潮湿和罪恶的气味,偏执和革命的气味。容易腐蚀脸,所以我们应该遮住脸并迅速逃走,那些自由行走并玩耍的年轻人就是没有面具的暴徒。我迅速遮住了脸,似乎后面有急切和疯狂的脚步。
当步伐逐渐变化时,有人在勒住我的喉咙,使我难以活动。面具的覆盖使我呼吸困难,几乎窒息。在月光下,他手中的锋利的刀给我的脸带来了苍白而又充满生命力的闪光,然后锋利的刀削了下来,剪开了我脸上的面具。
我转过身,清楚地看着他。他没有戴口罩,穿着工作服。当他看到我赤裸的脸庞时,他发出一种动荡但具有感染力的笑声。他说我和他一样,而且确实一样,我可以看到他很害怕,动荡,聪明和安静。我冷静地看着我面前的暴徒,然后看着自己,我现在是暴徒。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刻有自我和爱的苔藓色项链,挂在我的脖子上,我像他一样大笑。
他甚至向我提到了鲍德莱尔的名字。我知道我不戴口罩时总是读他的诗集。他向我描述了鲍德莱尔(Baudelaire)对黑啤酒和裸露衣服的向往,以及对野兽的向往,我一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忍不住和他激烈地讨论,因为我的手指在沙滩上画出了细弯曲的波浪。
我告诉他,这些在这里被称为罪过。他对罪恶大喊大叫,罪恶,我们都是暴徒。自由被称为犯罪,自我暴露被称为恶心的欲望。他用未遮盖的,富有表情的美丽的脸看着我,他的眼睛在黑暗,汗湿的空气中闪着光芒。
他要我加入暴徒团伙。我知道这就像陷入了无尽的生命漩涡中。面具不再存在。人们大吼大叫。它隐喻了弱点之上的革命光环。
暴徒大声喊着,大喊大叫,那是我过去已经很熟悉的烂摊子: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梦想。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举手并走向光明。我们重新定义了罪恶。自由也获得了新的生活,在宁静的夜晚爆发,重塑了他骄傲的形象。死者的灵魂再次在面具外徘徊,渴望重新恢复。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夜晚。
这不是罪,这是“暴民”的胜利。我自豪地称自己为暴徒。我烧掉了所有的口罩,即使再遭别人嘲笑,嘲笑和指责,我也再也没有带着口罩出去,我再也无法满足我对更美好世界的渴望。幸运的是,我至少有一个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