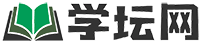一抹揉绉的忧伤_3000字
2021-12-18 05:04:42 5

“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击败了以不可一世的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创造了“美国也可曾入攻”的神话传奇故事,但在战争中所受的创伤仍未及时抚平,战后的窘态依稀残存。百姓们起早摸黑地劳作,却过着民不聊生、饥不饱食的日子。这使得我的降临有些落幕、唐突、失措。。唐突之余,便有了被奶奶揉皱在纸团里的一抹忧伤。
奶奶婚后三天,所谓的爷爷乘坐的飞机被国民党的敌机炸毁,奶奶的幸福便随同文思如泉的爷爷一起赍志而殁,予以奶奶留下的只是昙花一现过后的萧条与凄凉,奶奶把对爷爷的思念奏成一首日月轮回的哀曲,思念恰似哀曲的主旋律,起伏跌宕的音阶演绎出奶奶坎坷不平的岁月。固步自封的奶奶顺理世俗,一边吟唱着哀曲,一边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一晃就是十来年。
亚奶奶刚来我家的日子也不见有多大的起色,追究其原因为:我父亲的姊妹多,而且年龄小。但爷爷勤劳、精明,每天日月三光之时,便起床扛上100来斤的重担徒步去100多里开外的城里做些小买卖。晚上又披星戴月赶回家,家里则有贤惠能干的亚奶奶打理,日子自然有些辗转。经过爷爷与亚奶奶几年的努力打拼,家很快就在当地小有名气了。爷爷购置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田地,生活已不愁吃穿。每逢青黄不接之时,善良的爷爷总把家里在多余的粮食不收取任何费用都预借给周围的贫民,大多数的时候,爷爷还得担心借主是否有力气扛回家,且吩咐亚奶奶备齐饭菜,必定借主酒足饭饱之后上路。
爷爷不再与人世较劲了,亚奶奶的日子就像“日子”中的“日”字,便少其中间一横,不管如何努力,总是支棱不起。当时,国内革命依然还在继续。革命是激进的,但受当时文化水平的制约,使得革命的宗旨在传达的过程中被无意思地扭曲变形,革命的痹病暴露无遗。
接着,便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士:一件外套披在肩上,衣襟上插着笔;双手反背于身后;高高垄起的腹部,嶶微向前倾。但很清楚看得见,里面塞的不是知识,而是油汤与蒙昧;一双双贼溜溜的眼珠四处乱转,企图发现什么。
下午,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士运筹帷幄,预备为亚奶奶的勤劳行为举行“表彰”大会。所谓“表彰”大会,实则批斗会:将“犯人”押上示众台,先用绳索来个五花大绑;然后在头上扣上一顶用报纸折叠成的1米多高的毡帽,毡帽高耸云天;再用毛笔在帽沿上挥上“罪该万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字样。然后召集全村男女来鉴赏,情节严重者,则还会吃棍棒之苦,受皮肉之伤,亦或拖着疲惫的身子,敲着锣,打着鼓,排着浩荡的队伍,满村行游。至于为何要用绳索将其五花大绑,以防万一遇到个托塔天王反乱,理由可谓充分。但至于高耸云天的毡帽,我不得理解。闭目冥思,好怪的念头又涌现脑海。好使“犯人”犯颈椎之疾?我寻思。即便这般,轻轻的报纸怎能所奈何得了的?还不如改成金铂之物。看来,我列举的这些都不是目的所在,那便是取悦于愚昧罢了。而对于不公平的处罚,恐怕只有愚昧才开得心来。
莫道岁月无情,青春原本脆弱。20世纪70年代,我的灵魂追逐着目标躯体一同来到这银灰色的人世间,我用母亲赐予我的温热的血液和幼小的躯体去感受人间冷暖。那时的亚奶奶已老成了一棵大橡树,脖子上的皮一耷拉一耷拉地往下松懈着,原来笔直的身体弯成了一道弓,银发长飘,宛如白魔女。她的动作也变得有些木纳而又踌躇不前,就像录音唱片卡带,反复倒腾好多次才能顺理成章完成。但当时在我看来,她依然美丽慈爱,处处充实着我的视野,为银灰色的人生点缀绚烂色彩。
福运并臻,这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我没多大的本能去改变什么。生活中尽管有亚奶奶这堵为我遮挡雷电风雨的龙背墙外,家庭的拮据和父母亲整天无休止的争吵,使得我童年的脚步走着走着、跑着跑着,便飞了起来。飞越童年的海洋,将无忧的足迹撇在天边,落定的是一辈子沉稳、沉重的包袱。
同宾客一起用过餐,便启程回家。路途并不遥远,嗲孙二人却走得甚是仔细。奶奶随儿背着我,走几步,退几步,像录音唱片卡带;随儿又牵着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马观花。如此往复运动,必定也要疲惫的,于是嗲孙二人干脆在一棵“抱抱杨”下盘膝而坐。
有时候,金钱不等于感激,但转载了感激的金钱是一定值得去珍藏的;而珍藏并不只是加把保险锁那么简单的事,要存放于心灵幽深之处,用肺腑去感受、去接纳……
我的出生是在成立的早期三大体育运动:“土地革命”“土地革命”“蟑螂和革命”不是一个窗户,衣服非常好,人民,全国,国家,国家。
虽然“反美国援助”战争击败了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权力,“美国也可以攻击”神话传奇故事,但在战争中,创伤仍然是愚蠢的,在战争嗜好之后仍然存在。我在人民早期起床,但我经过人民的生活,不开心。这让我到了一些结束,唐军,我迷路了。 。唐军结束后,我已经在纸质组的论文组中皱纹。
每当你想到你的祖母,所有悲伤都会,所有恼火都会在皱纹的纸质小组中流血,让我的良心再次感到不安。奶奶的命运已经制作了一个黄色的莲花,如果有一个痛苦的黄领,那不是黄莲的捍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