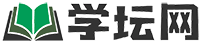那棵树下
2020-12-15 21:12:33 29
我记忆中的刺槐总是郁郁葱葱。我仍然可以看到充满阳光的瀑布,就像无数的下午洋溢着相思香水一样。

在祖母房子的小院子里,长出这么高的刺槐树真是一个奇迹。刺槐开花持续十英里,香气扑鼻,这也是一个奇迹。高刺槐树就像张开opening石。邻居经常说这是一棵有福的树。
就像大多数诗人所描述的桥梁和月光一样,带着故乡的困惑和忧郁,刺槐树留下的时间有些醉酒和涩涩。
奶奶正坐在树下,面对树枝和树叶所掩藏的细微光线,将一根线穿过针孔。一副老花镜在光的反射下缓缓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奶奶用力地抬起头,金色的光芒跟随着额头的细腻纹理,轻轻抚摸着,她没有抬头看着我,但似乎能感觉到我存在,只温柔和善意地说:“过来坐下。”
我一坐下,奶奶就开始定期讲故事。奶奶讲的童话故事不多,永远都是“匹诺曹”-这仍然是我的一本漫画,“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老人叫皮帕诺,有一天,他雕刻了一个一块可以哭成木偶的木头……”奶奶的声音温暖而醇厚,她的方言口音很奇怪,听到“ puchi”时总是让人发笑。每当我笑了起来,奶奶的口音就会变得越来越重,她的话变得很热情,就像一个孩子在吃糖果一样。
我偶尔靠在树上,偶尔靠在她上。偶尔抱树,偶尔抱树。树木的纹理被阳光反射,它的生活有些沧桑。但是我认为这看起来像奶奶的细线,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只是最好的样子。
奶奶还没说完就说完了。她pur起嘴,向我展示经过的线,好像她刚刚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我拿起线,拔出了她长时间穿的线。我想再次放入,但线蓬松,无法穿。奶奶没有生气,拿了针,再次讲了这个故事,然后穿了线。
现在想起那棵树,似乎它仍在我的记忆中。小桥,流水和人们的房屋就像每个流浪者心中的影像一样。怀香的淡淡香气,无论何时何地,都使我再次回到那棵树上。
有人曾经说过,无论脚步声不停,内心都必须保持。时间在改变,生活在改变,甚至记忆也会在改变。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拥有它,某些事情从未改变。
阳光普照,花香扑鼻。我记忆中的那棵树以最原始的姿势出现。记忆中的那个人,倚在树上,微笑着,突然转过头挥了挥手:“过来坐下。”
“嘿,就在这里。”我tip起脚尖,热情地招呼我,冲向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