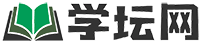小说内容节选素材
2021-09-07 20:11:41 42
(一)谁是残障
1971年8月的深夜,那晚要回家时正下着雨。
我开车开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时,狂风骤雨击打着我的车子,突然手上的方向盘猛盘猛然一震,车子失控突然偏向右边,同时我听到可怕的爆炸声。
我奋力把车停在湿滑的路边,想到整个情况便愕然不知所措,我不可能独立换下爆胎,完全不可能!因为我的运动神经受到感染,病情逐渐恶化,起先是感染到右手右脚,然后是另一边。
虽然生病,但是车上装了辅助的器具,我还是一样开车上下班。后来我想到也许路过的车子会停下来。
但我随后就打消了这种想法,为什么他们要停下来?我知道就连我自己都不会停。
然后我记起马路边不远处有栋房子,于是我发动车子,缓缓前进,开进泥土地。幸运的房子的灯光正欢迎我,我开进车道,按了喇叭,有个小女孩开了门,站在那里看着我。
我摇下车窗,大声说车胎爆了,需要有人替我更换,因为我跛脚,无法自己更换。
她进入屋内一会儿出来时穿着雨衣,带雨帽,后面跟着一个男人,愉快地跟我打招呼。
我舒适而干爽地坐在车内,觉得在暴风雨中奋斗的男人和小女孩很可怜,没关系,我会付钱给他们。
雨势稍减,我摇下车窗看换胎过程,他们似乎动作很慢,我开始有点不耐烦,我听到车的后边,传来金属的清脆碰撞声和女孩的声音:“爷爷,这是千斤顶把手。”
老人低声含糊地回答。
车子慢慢被顶了上来,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声响及车后低声的对话,最后终于完工了。
千斤顶移开时,我感到车子撞到地面,接着是行李箱门关闭的声音,他们就站在车窗口。
老人在宽大的雨衣下看起来很虚弱,小女孩大概8岁或10岁,她往上看我时,快乐的脸庞带着微笑。
老人说:“这样的天气,车子出毛病很糟糕,不过都修理好了。”
我说:“谢谢!那我该付你多少钱呢?”
他摇摇头说:“不用,蒂喜雅告诉我,你的脚不方便,我很乐意帮忙,我知道如果是你,你也会帮我忙的,不用收费,朋友!”
我拿出一张五元纸钞:
“不!不!付账是应该的。”
他没有要拿钱的意思,小女孩靠近车窗,低声地对我说:“我爷爷看不见。”
接下来几秒钟,我只感到羞愧和无比的震惊……
我从未有过那种强烈的感觉,一个盲人和小孩,在黑暗中用湿冷的手指去摸索螺栓和工具,而他的盲眼所带来的黑暗恐怕至死才能终止。
他们在风雨中为我更换轮胎,而我却坐在暖和舒适的车中。
谁是残障?
他们道晚安离开之后,我不记得自己坐在那里多久,但时间长到足以让我好好地探索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出所有恐惧不安的症结。
我了解到以前的自己,心中只充满了自怜,自私,对别人的需要很冷漠,不体谅别人。
我坐在那儿祷告,谦卑地祈求力量,祈求更能了解,更透彻洞悉自己的缺点,也祈求信心,祈求圣灵的帮助,以克服这些缺点,我祈求上帝降福给这位盲者和他的孙女。
最后我把车子开走,心里仍然颤抖,精神上却很谦卑。
继续走自己的路
两个人拖着很重的皮箱到了公交车站等车,年长一点的对年轻的说:“你出汗了,擦擦吧,”年轻的就用手抹着额头上的汗水,一中年人经过看到了这一幕,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面巾纸递给年轻人说:“给,用这个擦!”年轻人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中年人:“多少钱?”
中年人说:“不要钱,给你拿去擦汗!”年轻人仍旧固执的说:“你就说多少钱吧?”中年人依旧说:“要什么钱,就是送给你擦汗!”年轻人看了年长一点的人一眼,年长一点的人暗示的摇了摇头,年轻人很干脆的说:“不要!”中年人上下仔细打量了一下年轻人,又打量了一眼年长一点的人,心里在说“看这两个人也不像是有钱的主,再说了有钱人也不会费这么大的劲自己拖着这么沉重的包箱,中年人再次把面巾纸递到年轻人的面前:“拿着吧,真的不会要钱的!”
年轻人把脸扭向一边,一副懒得打理的样子摆着手说:“不要,快拿走!:”中年人有些生气了扭头就走:“不要拉倒,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没走多远就听着年轻人跟年长一点的说:“真是要了他的那点纸,还定要讹咱多少钱呢!”那年长一点附和着:“就是,多亏了没要,哪有白给的东西!”中年人回头站那了好一会,直到那两人上车走了才转回身叹了口气走自己的路了。
有时想做一点好事也难,这也不能怪他们,这都一些负面影响造成的,不过但凡是好人是不会计较这些不被理解的尴尬局面的,他们还会走自己的路,把好事做到底。
(二)“穷人”
一个人若是喜欢贪、占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或物品,常被别人讽为爱小。这是一种很不好的性格和品德,而且与人的贫富、地位关联不大。
因为爱小,竟然能使得富人变“穷”了。我就曾经听说过一件此类的事情。
话说进入本世纪后,中国大地上几乎所有的城镇都刮起了疯狂的房地产开发风暴。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最终富了两大块:一是地方政府,吃了最肥的肉;二是城中村改造涉及到的村民。至于开发商,就单位收益而言,顶多排行老三。
单说城中村改造,但凡一个坐落在城市版图之内的村落,一经改造,一户村民分得两、三套住宅算是少的,多的能分五、六套。
这些村民们太幸福了,他们房子多得住不过来,就租出去一套、两套的,每月(或季)收房租,可比当年的老地主富有多了。
不过,一夜暴富了的村民却有的变得更“穷”了——他们不是“穷”在物质上,而是“穷”在心里。
现在,城市里日常生活大多都是烧天然气(或煤气),价格挺贵的,怎么办才能省钱呢?于是,那些暴富的“穷人”中有智者,“穷”则思变,竟然想出了离奇的“省钱”办法。
先是有一家最聪明的人,住进新居后,经过反复思考,想出了一个极好的办法:让燃气表不走字——简单,把气表给摘了就行。这种先进、有效、而且简单的经验传播很快,一时间邻里之间纷纷效仿。
说起来,也怪燃气公司麻痹大意,由于燃气表是插卡式的,输进表内的气量用完了,就会自动停气。燃气公司太信赖先进的仪表了,没有想到竟有聪明人会抄近道儿,所以,他们在短时间内愣是没有发现这种聚众“揩油”的行为。过了好长时间,直到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入户安检时,这种“揩油”行为方才暴露。
偷用燃气是违法的,于是,燃气公司将这一众用户告上了法庭。按照法院的裁决,这些用户都赔偿了燃气公司一笔费用(包括燃气费和罚款),是赔、是赚他们也算不清,因为没有表,就没有计量数据,燃气费是燃气公司根据各用户的人口多少以及摘表的时间跨距估算的,是个大概数,罚款则是按燃气费的一定比例给出的。
经此事件之后,燃气公司学乖了:他们每个月入户“安检”一次,名义上是安检,其实更主要的是看用户有没有偷气的行为!
那些“穷人”虽然交了燃气费和罚款,但是心里却并不平衡,暗想:“那些贪官污吏捞了那么多都没事儿,俺们就偷了点儿气,就给告上法庭。”其实,他们想错了,他们遇到的只是毛毛雨而已。
对于贪官污吏们(同样的,也是“穷人”),应了那句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以前有大黑伞给遮着,他们倒是挺安全,而现在党中央一厉行反腐,那些贪官污吏们可吃不了兜着走喽——被查出来的家伙不仅丢官罢职,贪多少也都得吐出来,轻的住班房,重的连小命儿都保不住;那些尚未被查出来的主儿们,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估计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终日提心吊胆的,简直快愁死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三)勇者无畏
阿智记得自己以前上小学时,有一次暑假期间,一位邻居大姐姐跟男孩子一样,打着赤膊从院子里经过。结果,她的“勇敢”举动招得同楼的一位叔叔魔怔了,不仅脑袋上挨了他媳妇一蒲扇,还遭了媳妇一顿抢白。
别以为这位大姐姐神经不正常,其实,她一点儿毛病都没有,只不过是天生的质朴、无邪的性格决定了她敢想敢做的行为。
试想一下,一个豆蔻年华的大女孩儿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像男孩子们那样裸露,她还有什么不敢为的?
在阿智的记忆中,这位“勇敢”的大姐姐,有两个名字:大名和小名儿,全是满带女孩子特点的。她除了四大(大个子、大脸盘、大嘴岔、大胆儿)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很能说,而且既不是胡搅蛮缠、也不是闲言碎语,讲起话来颇有条理。由于她的记忆力很好,讲话时引经据典、背诵书上的段落,竟然连喯儿都不带打的。
在口才好这方面,她显然是兼收了父母的长处:他的父亲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文质彬彬的,跟邻居们很和气,他平时话很少,若说起话来却是有条有理的;而她的母亲,就活脱脱的是一位“阿庆嫂”,嘴快得就像打机关枪。
大姐姐出过一次糗事儿。她母亲是个大高个儿,上初二那年,大姐姐已经跟妈妈差不多高了。一次,她们娘俩儿商量好在家摔跤玩儿,女儿的力气大,把妈妈按倒在地上,她赢了!谁知妈妈突然翻了脸,坐起来扇了女儿一耳光。事后,大姐姐跟伙伴们提起这件事儿时,还是气鼓鼓的:“大人就是不讲理,说得好好的,是闹着玩儿,可是人家输了就翻脸。”估计此后大姐姐再也不跟母亲摔跤了。
上小学时,阿智与大姐姐见面的机会还比较多,等到阿智上了初中,由于学校常组织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军、拉练、去分校等等,他在家的机会就少了,而这时那位大姐姐已经工作了,所以他们就更少见面了。
后来,大姐姐家搬走了,从此阿智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儿。
不过,若干年后,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阿智似乎又觅到了她的踪迹——那是一位与大姐姐同名同姓者。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城里有几家企业成了改革的排头兵,这些企业及其负责人不仅在本市出了名,而且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了名气,当年全国著名的企业改革者里就有他们的名号。
在某位企业家的改革事迹中,提到了阿智熟悉的那个名字,不过,她是做为反对改革的对立派而上了报纸的。据报载:她当时是工厂团委的干部,为了维护下岗职工的切身利益,勇敢地站出来与力主大刀阔斧改革的厂长对着干,被视为“钉子”。
可喜的是,后来她没有被“消灭”,而是被吸纳进了新组建的厂领导班子。
虽然没有在宣传材料上见到有关她的图片,但是阿智的直觉告诉自己,那个女干部就是大姐姐,因为这种作为太符合她的特点了。
俗话说:勇者无畏。也只有像大姐姐那样从小就那么“勇敢”的人,才敢跟当权者对着干!故而,报纸上提到的人物不是她还能是谁?!
(四)放飞
潇梦原本有一对儿小鹦鹉,可是她自己不小心放跑了一只。于是,她开始跟父母“蘑菇”,争取再给配上一只。后来,她终于如愿以偿,鸟笼子里又有两只小鹦鹉了。
不过,两只鹦鹉毕竟不是一家,所以,最初的几天它们相互之间虎视眈眈,甚至还常打斗。过了几天,或许它俩都想明白了:自己和对方都是天涯沦落者,何必再相互为敌呢?于是,它们消除了隔阂,开始互相啄弄羽毛、互相依偎。
过了一段时间,也不知是何原因,其中一只鹦鹉开始用嘴揪自己的羽毛,特别是茸毛,每天都揪,后来胸前、翅膀根上的羽毛都被自己揪光了,就像是光着膀子的伤兵似的,样子非常难看。
这时,潇梦已经升入了初中,父母跟她商量,放飞鹦鹉吧,叫它们获得自由。潇梦虽然不情愿,但是她毕竟已感到来自学习上的压力明显比小学大得多了,再像以前那样为小鸟儿分心是不可能了,所以,就勉强答应了。
这天是星期日,放飞鹦鹉的工作正式启动:鸟笼子被挂在阳台外面,然后小门也被打开了。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了,小鹦鹉们依然还在笼子里呆着。不过,它俩始终在一个劲儿地窃窃私语,似乎是在讨论出去好、还是不出去好,或者是在商量由谁打头阵冲出去试试。
最终,那只光膀子的鹦鹉将小脑袋伸出笼门四下张望了几次,然后跳到了笼子上面,对着笼子里面的另一只鹦鹉啾啾了几句什么,便展翅飞走了。又过了一会儿,笼子变空了,两只鹦鹉终于全获得自由了。
它们以前住在笼子里,虽然空间极其狭小,可是毕竟不缺吃、不缺喝的。现在,它们远离了笼子的束缚,可以自由地飞翔了,但是必须自己打食、找水,还得设法遮风避雨,……,很多的困难在前面等着它们。
与人相同,世间万物都渴望自由,可是须知自由与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没有了后者的支持,自由就是虚无飘渺的,不过一张空头支票而已。
对于那些尚未脱离父母呵护,羽翼未丰的大孩子们,抽空思考一下,不久的将来怎样通过自己辛苦与汗水的付出,来换取一点点自由,其实是很现实的事情。
(五)脸面
张山觉得自己病了,他这种病别人极难察觉,只有他自己知道已经病入膏肓了。他的病不痛不痒在脸上,他对着镜子瞧这张本来没病的脸,怎么就会病了那?
张山想起,他的病因是和小侄子玩了一天。那一天他的脸没有刻意去伪装,而是像小侄子一样高兴的时候就哈哈笑,难过的时候就拉着脸撅着嘴。这一天他感觉紧绷着的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防松,这一放松不要紧,第二天他上班的时候发现脸不受控制了。见到领导他本应该露出卑微地笑容,可他去露出了讥讽地嘲笑,虽然他心里是这么想要嘲笑这位一无是处的富二代,可这绝对不能显露在脸上,不然饭碗不保。还好领导高仰着头没有发现,越他而去,他却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发现自己的脸面无法控制,心慌不已,不敢抬头,低着头猛走,却差点撞在一座肉山上。他连忙后退赔好话,这座肉山是厂里的财务主任,领导的小姨子,在厂里呼风唤雨很有权威。
张山每次见到她都会露出一副惊艳的表情,然后夸她:“燕姐,你又瘦了。”
可今天张山的脸病了,他嘴上说:“燕姐,你又瘦了。”可脸上的表情,却是憋不住地笑。
“肉山”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对他的表情很不满意,一拧身子走了。
张山知道他是彻底得罪了这位大人物,他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悲伤的表情。心想,我不能在继续走了,这张脸会把我的情绪全部外泄,如果走下去,遇见主任,那个干瘪的色老头,还有妩媚的职员小叶,他或是讨厌或是喜欢的情绪都会写在脸上,这可怎么得了。他赶紧给领导打了一个电话,说生病了要去医院。
领导很爽快地给了假,末了说了一句:“不过这个月就要到月底了,你的满勤奖金可就没了。”
张山真恨不得摔了电话,冲进办公室狠狠揍领导一顿,可他要是想生存,想着这里赚钱,就只能忍着。这时他的脸上一定写满了不满地恶毒,他没加控制,心里甚至大叫爽快。
爽快归爽快,他还得面对现实。他奢侈地打车来到了医院,挂了一个面部神经科,没想到来看病的还挺多,他排在长长地队伍后面,看见各式各样的面孔,小声问前面的小伙子:“兄弟,你得了是啥病?”
小伙子无奈地道:“面部不受控制,因此我还丢了工作。”小伙子的脸纠结成了一团。
张山皱着眉问:“这些人不会都是这个病吧?”
小伙子点点头。
他立刻觉得轻松了很多,原来他不是第一个得这病的人。
想想他觉得可笑,原来人心里的想法是不能表现在脸上的,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会给生活和工作带来无尽的麻烦。
轮到他时,他走进诊室里,一位面无表情的老大夫坐在里面,看也不看他说道:“你的病叫孩子面,顾名思义,就是说你的脸又回到了孩子时期,会随着你的喜怒哀乐表现情绪。而人长大之后,由于经常伪装自己的情绪,心和面之间的神经就会断掉,人的脸面就容易控制喜怒哀乐了。你之所以发病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刺激,或是和天真无邪的孩子有过接触,而放松了面部神经,让它和心里的神经搭上了。我只有帮你把这两条神经拆开,你的病就好了。”
张山点点头,脸上露着了无奈的表情,因为他必须治,而且要尽快。
这个手术即快又简单,就是把一根线一样的东西塞进喉咙里,不到几分钟老大夫就说好了。
张山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欣赏的笑容连声说谢谢。其实他心里在打鼓,真容易和骗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