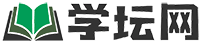古镇里走出的泥娃
2020-12-31 04:32:48 48
七八年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惠山泥人。那是在一个大学生民间艺术展上,在西北角不起眼的平方英尺桌子的拐角处,对两个满是灰尘的泥泞的婴儿微笑。当时,一个在无锡学习的同学跟我讲了泥塑。无论如何,很难产生惊奇和钦佩的感觉。因为虽然我在江苏出生并在江苏长大,但过去二十年来我从未听说过陶俑。我经常玩俄罗斯娃娃。辉山泥人是一个奇怪的名字。因此,带着这种奇异的新鲜感,我倚在人群外面的寂寞桌子的角落,仔细看了看这对泥泞的婴儿:

全身涂成白色,粉红色或红色,带有粗糙的水粉或某种未知的颜色。脸很胖,身体也很胖,就像香炉顶部的小弥勒一样。 “吉祥”和“如意”歪歪扭扭地写在一个简单的腹部口袋上。老实说,仅仅作为一个孩子的玩具可能还不够。
展览结束后,每个人都像往常一样购买了一些物品作为纪念品。我的同学刚刚订购了一对泥人给我。展品店的老板是一个衣冠楚楚的人。他拿走了同学交出的两张小钞票,从陈列架上捡了起来,最后小心翼翼地捡起两对,然后喷在浅蓝色的丝绸上。我用了清洁剂,来回擦拭这对胖娃娃几次,然后转过身看着,然后换成一块橙色的干丝布擦干,然后小心地放入红色的。在盒子里,关闭翻盖并在盒子上系好蝴蝶结,然后再握在手中。...这对不起眼的陶俑可以由优雅的店主恭敬地送达,我请他们开始看一下。看着这个小木箱,静静地躺在书包的底部,我突然感到一种神秘感。
回到家后,他愿意打开盒子并仔细检查。像店主一样,他小心地发现了红色的绳子,小心地打开了盖子,并小心地放置了两个陶土娃娃:
每个雌性和雌性中都有一个泥泞的婴儿,皮肤光亮到极致的白色肉,红色的腹部紧紧地附着在胖乎乎的身体上,这样一来您就可以在角落看到一些褶皱;头发是黑色的。纯粹地,额头前部的自由折断的刘海似乎并没有用人造毛笔刷上,而是好像确实附着了几根头发。轮廓和层次清晰明亮地分散;尤其是那些让人喜欢的人。一个小婴儿的两颊和眉毛之间的小朱砂痣上的肉红色,不太大或不太小,恰好位于两个月牙形眉毛的中间,整个娃娃看起来真的很敏捷;至于莲root节,他的小臂和小腿更渴望捏和咬。
我迷上了这两双欢乐的眼睛,陷入了遐想。这是苏乌软土地深处的柔情,还是Li湖微波发出的温暖的声音,也就像秋雨洒在惠山无边的树林上。山顶上的沙子不尽,香气澎sur。长江中流淌的河水和深秋的桂花气息使我想起了从山脚下农舍的屋顶上掉下来的落叶最原始的烟雾。 。
所以我想起了店主送我们出去时满意和不满意的眼神。是的,除了我同学的友谊之外,我怕我不会再改变这对泥土婴儿了。我也会仔细地封装它,但是我不会以如此柔和的眼光看回辉山古镇出来的手工玩具。我能想到的这些话似乎仍然很难表达黏土雕像的魅力:回望过去并感到温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难以平静下来,但我却产生了失望的感觉。彼此相见时自责。这样一个具有艺术魅力的黏土宝宝从未听说过它,并且缺乏玩黏土小雕像的真正内涵的启发。如果粘土小雕像的魅力不时在我心中浮现,那肯定会影响我对吴楚地区农村生活的感受。而且体味也会影响文本的色调和质感。每当我面对西城河的道路时,都不会感到困惑,并且灯是红色的,感觉到铜的气味从文字中流出来,并且同样是无病的吟。所以我进一步认为,如果文字中有黏土的味道,那么叙述的古代故事将充满黏土的魅力...
直到后来,我才来到古镇,终于再次看到了辉山泥塑,并为辉山泥塑写了一首歌,从那时起,我就感到宽慰。
后来,我想在其他地方看到泥塑,但很难得到我想要的。但是三年后,我有幸再次在无锡工作,距离无锡古镇只有不到3公里,这使我沉迷于泥塑。那天,无论是一个红白相间的胖宝宝,还是一个蓝黄相间的女孩,或者是坐着,躺着,跳着,微笑着……他们都喜欢这一切,而辉山泥塑的独特魅力最美。路过的人们的感叹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应。实际上,泥塑的纯正和真实的手工艺,有多少游客可以了解和想象,为什么他们会停下来欣赏这么多呢?我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劳动和智慧的光辉,一种在诸如西城的辉山这样的古老而长期的文化城市中流传的深厚的积淀,它是将当代人深深地埋在他们心中的一种。尚未被世俗的世俗或奢侈艺术所吸收的神经被激起。我认为山脚下的简单手工艺可以被视为民间艺术的最原始典范。
那一刻,我很感动,自从宋代以来,无论明清,甚至今天,这组手工艺品都是用这种方式制作的。继承了过去,这种工艺世代相传。至今,我站在这个古老城镇的泥土上。我徒劳地试图避开所有人的视线,躲在角落里享受精致,并与现代社会中具有不同审美观的人们保持亲切的距离,并试图消除因文化兴趣和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孤立感。押韵……这让我一阵震惊。就像这些人走过我所追求的浅薄文化水平一样,我突然意识到,我主观上打开的鸿沟就像是我自己的一种肤浅。一种是没有意义的,一种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