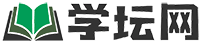宋晓杰散文诗组章《以沉静,以叹息》
2021-10-18 13:03:31 21
以沉静,以叹息(1)
作者简介:宋晓杰,笔名飒飒,1968年6月生于辽宁,现供职于辽宁省盘锦市作家协会。17岁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已出版诗集两部、散文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发表插图若干。中国作协会员,辽宁省签约作家。参加过第十九届“青春诗会”、第二届全国散文诗笔会。
曾获辽宁文学奖诗歌奖、辽宁散文十年奖、全国散文诗大赛“女娲”奖、第二届老舍散文入围奖等奖项。有多种作品入选各类选集。
生如夏花
一生何其短促
短如一滴泪的由热到凉
一日又是何其长久
长如一头青丝的千年一苍
——《行走在紫色的忧伤里》
沿着墙根儿,你匆匆地转过街角,如一阵迅疾的风,身后撒下点点花种,转瞬之间一片繁盛。
你手中的细花阳伞,低低地遮住心事,明明灭灭,无人能懂。
把一世的灿烂在一个夏天毁掉。
把一生的夙愿在一个夏天兑现。
没有怨尤,没有悲痛。
提着花灯,把哪里照亮?你细碎的脚步正好踏上薄雾的清冷。
提着花灯,把谁人唤醒?你温软的语气正好呵护着寥落的晨星。
花瓣儿颤栗,瑟瑟地抖动,最后一滴泪将在哪里谢幕,最后一声叹息又要在哪里登程?
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
夏太喧闹,确实需要静一静。
要开放,你就悄悄,即使虚掷了花期;
要凋零,你就默默,即使浪荡了华年。
把野花领到原野、山冈、河畔,让它们在最光鲜的时候消失,让它们看到万物的博大。
我一遍遍地诵读着铭文,一遍遍想着笑盈盈的野花,心里一阵阵轻松和感动,没有悲情。
游戏人生
除了靠不住的所有
还有什么值得依靠?
——《路过幸福》
折些枝叶,编一顶柳条帽,紧握自制木枪,学着大人的样子匍匐、呐喊、冲锋,不怕吃苦受罪,流血牺牲也变得分外神圣。
而和平之光熠熠照临,没有了硝烟和烽火,有多少人还葆有可贵、未泯的童心?
做的不是说的,说的不是想的。
这连接处的沟壑和断层拿什么填平?
我的喜悦恍惚,恐惧深重。我笑不敢露齿,恨不敢出声。惟一的想法就是把游戏作真,看不出破绽,一本正经。
我不世故,只想用毁灭的方式把自己打碎——粉碎在你心目中的形象,让你看清满地尖利、丑陋的碎片,息止你经久的赞颂,让你潮涌的心一点点回归从前的宁静。
任凭责怪、诘问,任凭愤怒、骂詈。
我涨红着脸庞,一言不发。
看你童年的背影消失于曲折的小巷尽头,我拾起被你忿然撕烂的风筝,泰然自若,忧伤灭顶。
在一己的悲欢中,珍存起一个飞天的梦。
时光怎样的深处
黑夜,除了你
我还能怎样
与世界言说
——《最后一个夜晚》
黑洞,席卷着旋风,探向幽深的地宫。
魔盒,神秘莫测,紧锁着无以明状的灾难和怒火。
原始森林,亿万斯年的沧海巨变,侏罗纪、煤炭、鱼化石、松油里的飞虫,无言的明证。
日月星辰日日是为谁落?
葛蕨藤萝年年是为谁生?
我是一节一节错过的火车,是一浪一浪殒灭的花海,是无本之木,是空穴来风,在薰衣草的香气里有长久的睡眠,短暂的安宁。
我在时光的深处等你,在一息尚存的针尖上等你,让一滴水放大快乐,让一丝光照亮前程。
想起辽远的世界,你的哀愁多么细小。
想起蚂蚁的努力,你还有什么理由悲微?
黑夜是最安全的居所,黑夜是最纯的阴谋。
在时光的深处,我祈祷……
遗忘之光
终是短暂,终是遗弃。
在站台,在港口,在可能
安放梦的地方,除了理智、责任和
广义的爱情,其实什么都不存在了
停机坪上阳光耀眼,泪光中
一次次把你错认:遗忘变得如此简单
——《记忆(三)》
还不是傍晚,在思念的维度里挣扎、浮沉,如一只起落频繁的小竹筏,找不到岸。
旧事重提,意味着对自己的背叛,扯起大旗,分劈蜂巢的泡沫,剥夺那些虚张声势的生活。
记忆是最信不过的,它总是在最动情的沉浸之时猛击一掌,让我还阳。待转过头时,已辨不清失去的方向。
“时间不能使失去的再生,只能在永恒中享受天国的荣耀,或者遭受地狱之火的煎熬。”
温漉漉的黎明,苔藓和蕨类平添了湿气和丝丝凉意。声音虚弱下去,摇摇欲坠。
我黑瘦着面容,与自己的坚持道别。
无人喝彩
爱是女人最光鲜的
衣裳和肌肤
爱是骨骼和精髓
总之,除了爱
女人终将一贫如洗
干净得虚空
——《行走在紫色的忧伤里》
避开掌声和鲜花,避开追光灯和注目礼,避开威仪的车队和人流,避开能避开的所有,从热闹的氛围中悄然隐退,即使锦衣夜行,注定无人喝彩。
命运只给你一种可能,那么,就不应该说三道四,期期艾艾;生活只给你一种机会,那么,就不应该贪恋光华灼灼的舞台。简洁的衣服、朴素的菜蔬,波澜不惊的日子,才应该是沉实的最爱。
有多少人值得期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不得而知。未曾荒凉的心半合半开半开又半合。
经验的果子悬垂在高枝上,有蜡质的外衣包裹着,不会有丝毫的磨损,因其光其鲜,果子越升越高,被心悦诚服的目光越擦越亮。
给我时间!这创造奇迹的魔法师。沿着魔棍的指引,大地旋转成婉丽、激荡的唱盘,我们就是其中活泼、懒散的音符,和着轻风,不由自主地,把紧闭的嘴唇打开。
——在大地之上,我融入而疏离地活着,注定无人喝彩。
初秋的献词
这个春天转眼就过去了
我不爱说它像一个梦
可是它确有梦的特质:
甜美、寂寞、干净。不曾发生
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洗心革面
不得不一次次地忘却决心:
一边虚情假义地抒情
一边迎接具体的黑暗
——《囊空如洗地迎迓春天》
流水。香皂的气味。棉布睡袍。方格桌布。静止的苹果。
委顿的柳条。路灯昏睡的眼。这并非虚拟的场景,是永远不会涉足的过往,却用梦想和心碎把我击倒。脆弱的神经不胜酒力,何况又恰逢乍寒的初秋?
月将隐未隐,星将熄未熄之时,是麻质的清晨,爽适肌肤,复活身心。
当我像残荷破败悬垂,蝌蚪的文字环绕着我——我们已经隔开叫“年”的河流,莫测高深的尺度。
细雨。微尘。流转的眼波。鲜嫩的果肉。忽明忽暗的林荫道。那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惊奇于自己的坦然,没有恐惧,一张纸后面的熟稔。
你不是说过,要陪我去海边放风筝吗?
这轻言的许诺,使我一想到风筝就泪眼婆娑。
所谓的长久就是转瞬不见;
所谓的誓言就是不能实现。
这个秋天,我在病痛和心痛的双重摧残和威逼下,坐卧不宁,想把多年的芜杂收拾干净只能是企图。我不断地重复着:我过得很好!过得很好!真的。久而久之,便觉得自己果真过得很好——弄不清吞噬和蚕食哪个更疼!
春天还会有,梦还会有,但是,我推开家门,头也不回地冲进雨幕决不单单是因为你。
不需要任何一丝阴影的参与,我就是完整的草原、诗篇和明天。
夜晚来临之前
……满月。一滴硕大丰沛的泪
极力地为一个人噙着。人群中,
我忧伤着,却笑得最响
没有人知道真相
——《可能的爱情》
河床上,裸露的卵石没有棱角,它们的圆滑差一点儿把我绊倒。
很少的河水,然而清洌,还配有湿腥的水气和闪烁的光波。
还没有完全黑透,所有人的脸都被染上月亮的辉晕,在那样的情景下说话是不踏实的,犹如下桥的台阶并不是一步一个。
担惊受怕并不是小题大做,我们搀扶着,衰老着,直观得就像走过人生必经的水火。
平生没有见过那么大、那么圆的月亮,感觉那一角天空正在渐渐坠落。
我揪着心,一句话也不想说,但是,却忍不住发疯似地大笑,空洞而虚幻,妖冶而媚惑。
旅行车开走了,明明知道它会在下一站等着,还是免不了失落。
——夜空下,明明知道什么也看不见,而我们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
外省的童话
旧病复发
最好的医生只能是自己
…… ……
我不说我比白雪更白
你却比黑夜更黑
——《隐情》
大雪纷飞,妄想把整个世界吞没。
我却躲在水晶城里独自消磨。
去外省,在风雪交加的时节上路,去追赶童话中的火车。繁星点点,月桂树上挂满幸福的缨络。
拆开冬的细部,看雪花怎样制造了灾患,看我们怎样握住冰刀寻找对方暖热的心窝。
在那个万籁俱寂的黄昏,我走出庭院,走出固步自封的樊篱,粉饰的雪野中,惟有我的足音清脆,惟有我能听到雪花的耳语,在与季节的相互应答中,一阵阵地伤心难过。
一年又一年的大雪,把出征的道路封锁;
一树又一树的银花,把衰亡的激情凭吊。
仿佛从未走远。
仿佛从未来过。
“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把已死去或尚存的朋友珍念。”
好好活着。
干枯的野菊花
我不知道我是谁
但我知道
我是黑夜的新娘,是旧情的新欢
是一意孤行的执拗,是一往无前的勇敢
谁也不能阻止我的燃烧
——《烈焰》
沉香。有一点点野。
山风清爽,不避讳的微凉和寡淡。
清洁多楞的玻璃瓶,插上干枯的野菊花,附着上我不便多言的心性,一直站在窗前。
我不想回家,不想搅乱池水的生活,不想在最孤寂的时候熄灯,不想看栅栏内外收不好疑惑的脸。
悄无声息地出走,离开舞池和狂欢,像一块废弃的釉彩,藏在时光深处的草原。
我并不是难缠的孩子,我只是一桩小麻烦,是每天愈合又每天揭起的伤疤,坐立不安。有些微的真正的疼。
没有暗香也不要紧,留下野性的部分,留下精髓的部分,最起码,不想在苗圃中被搬来搬去,不想被一个心眼儿地溺爱,还美其名曰:爱怜。
——被蒸发掉的水分,是前世的苦难。
白杨树的怀念
一阵枪声过后
我们四散分离:
呼喊、放松,一顿奇香的晚饭
相似的季节和车辙,以及衰老
还有,如此轻易的夜晚
尘土把光阴和疼痛匆匆掩埋
——《打靶》
初始的发生都是模糊的,惟有记忆才能使有益的部分变得澄澈。时间抽象得成为哲学的内核,成为一个没有体温的冰凉铁器。
我怀念白杨树,就是怀念乡村,就是怀念一种不确切的生活。
那是三十几年前,奶奶牵着我的手,走在乡村道上。白杨林立,哗哗地细细地招云引风,却无心垂顾我这个愚顽的孩童——我们要去参加一对兄弟的婚礼,他们是英俊、憨厚的孪生。
几年前的白杨与三十几年前的,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直立的形象、响动、田野的衬景,还有它们无尚的光荣。
正午时光,压抑而寂寞,幸好有枪声划破。
我躺在滚烫的沙丘上,看云卷云舒,归去来兮。
孪生的兄弟是否健在,还有他们可爱的小妻子?庭院中的石磨是否依然残破,时盈时亏的粮仓是否经年未动?
孪生的年轮和秘笈刻在彼此的脸上,有几分滑稽和悲怆。
会有毫厘不差的人生吗?毫厘不差的沟壑、秋风和收成?
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枪声响过,起跑、长征、疲惫、冲刺……
在这又寂寞又美好的今生。
街心花园
也许是一棵树,或草
总之,一生都在与植物纠缠
也许不仅仅是植物
——《一生都在栽种一棵树》
你动了动身子,试图想离开那块斑驳的僵硬的土地,离开得远些——但是,没能如愿。
你的脚下是茂密的根须,缠绕着,纠结着,紧紧地附着着大地的吸盘,只把为数不多的枝条——长着稀疏头发的脑袋探出墙外,在一片开阔的秋阳里。
深重的呼吸伏在街心花园的琉璃上,是什么朝代的月光,冷漠、隔世、凄迷,还有深宅大院的阴湿霉气。
阳光普照,而你还贪恋着严冬,还忆念着某年某日的人面、桃花和春风。
——藕断丝连。
其实,我们无力选取一个方位,甚至连一个界面也不能自主,是它们在前进中选取了我们,并给了我们各自不同的胆汁、倒悬和敏锐的刺痛。
所以,我不应该在此夸夸其谈,浮泛地抒情:关于你的低迷、关于你的坚守、关于街心花园。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线团,越缠越紧。
——睡梦中,我的双手紧紧捂住号角的心。
河流的自白
我说慢下来就是另一种
疾走,就是在渐次沉陷的
大地上,跪下来
摊开双臂说:我爱!
——《走着走着就慢下来》
我是以行走的形象被人们记忆的。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慢或者快。总之,我不仅是一个表示宽阔意义的名词,还是一个动感十足的动词,被善用比拟的诗人抑扬顿挫地派上用场。但殊途同归,最后都无一例外地憾然走失了。比如光阴、青春、绵延的生命……
说与听之间,笼罩着薄雾的轻愁,任劲风也吹不散。
我是罪恶的渊薮、智慧的发源;我是喜忧参半;我是忠孝不得两全。
我不是灌溉田园,就是制造灾难,我一分钟也呆不住,但你们看我一直在呆着。
我用心良苦,所有因我而起的疾患、过失都不是我的初衷,都是因为我全神贯注、用情过专,像烧焦的岩、折断的钢,在流淌的过程中,失却了应有的尺度和方向。
但是,我更是宽容的,生死、荣辱、成败,都将涵盖,感激并且热爱。
我警醒地慢下来,大地一片苍茫……
秋色阑珊
把玫瑰床安置在哪里
恰好听到夕阳的沉坠
把玲珑玉戴在哪个指上
恰好匹配我的堕落
稻菽们挤在一起,温暖着
在黄昏中感恩、出神,无语凝咽
共同期待那道伶俐的寒光
——《黄昏时分》
毒酒、砒霜、美女蛇、罂粟……在所有的剧毒中,我选取最小的一粒,慢慢呷下,尔后,在幸福的最高峰滑向深渊,等待复苏,等待悲壮地生还。
温存地自缢!
妖冶地灼伤!
已是秋分时刻,露水开始造访清晨。在颤动的草尖上,沁凉的秋意微寒,饱满的生命承受着意想不到的孤单。
树开始大面积脱发,退去烦恼,改头换面,以残忍的方式,使希冀得以保全——要多艰难有多艰难;要多勇敢有多勇敢。
“夜空中撒满了闪光的金星和银星,它们代表了幻想之火,只在夜的深沉的葬礼上才闪闪发光。”
背负起远方、怀想和沉重,在醉意阑珊的秋色中出发——如果在即将冰冻的池塘或河畔,你踯躅着自责的脚步,会不会有一棵白杨令你的心不安地颤栗——余晖中,它光秃秃峭楞楞的枝桠暗藏着温情,举棋不定。
露天电影
细雨、幽香、灵动的眼波,审慎,
羞赧;平凡的碎片
却是一个人的星辰。黄昏
来得正是时候,在旷野中,
足音清澈、荒芜,大地陡然浑厚
朝着一个方向呜咽,日夜满怀生的理想
——《纪念》
你还坐在黑暗中看着电影,是露天的那种,是黑白的那种,即便表现的不是雨天,也有“阵雨”哗哗地下着,人的脸和身子有一点扁平。
先是很多人,嘈杂的吆喝声、奔跑声、心不在蔫的咀嚼声——那声音正好遮住银幕中主人公羞涩的相逢。
后来,陆陆续续地减下去:一个个人物、一处处场景、一颗颗星星,缓慢、雾霭、下坡……无知无觉的过程。
剩下多余的我,在空白中漫漶,迟钝地被记忆漂白,旋转、寂寥、茫然,欲哭无泪。
黑暗中,白色的幕布似大地之门高悬。
我坐在原地,痴痴地等着电影慢慢演完,等着散场的喧沸中有人焦急地呼喊我的乳名……
四野空寂,而我,还沉在苦海和滚滚尘埃之中……
旋转木马
我不得不在生活的边缘徘徊
一圈一圈一圈一圈
推着小小的精致的磨盘
——为了疼为了不疼
为了爱为了不爱
——《一天中或许有时能会晤自己》
童年的木马尚在,而无忧的时光已经远去……
旋转的木马不说话,在公园的一角奔跑着,却怎么也跑不出寄居的草原。慢动作,像缓慢的衰老,升起,降落,寸步难移,却又重蹈覆辙。
旋转的木马不回家,在黧黑的山峦间蛰伏着,却怎么也不能被更浓的黑淹没。径自站着,退回到树的形象,敦厚,沉默,死心塌地,却又流离失索。
木马旋转,像一盘小小的磨,像我们不能削减的剥离。
一阵铃声响过,木马重又开始了茫然的欢歌。
大地飞旋,沉沉陷落……
女中音
绢:是不是没有未来的初恋
心境中的春天
激活了一生的绝唱
——《绢:春的心情》
不想高上去,也不想低下来,是稳稳当当的中音区,登堂入室。
在圆弧形的光晕里,你款款而立,不走动,也没有夸张的表情,曳地的长裙表明你不饰张扬。
与激越、尖峭不同,浑厚、浓醇更能震颤心灵,更能牵引出哗啦啦的流泉。点染上几枚经霜的枫叶吧,让它在山岩间脉脉流淌。
远处的手鼓声声,柔和的月光、空出的宽敞,正好被恩宠者贴心收藏,磁石般的力量。
忽略容颜!容颜是靠不住的,容颜是一次性的支付。而歌声不老,惟有歌声在身前身后传扬。
与海誓山盟、海枯石烂的初恋绝然不同,歌声是第一眼的信赖和托付,是秋季里微小的疾病和滑爽,是一条浓荫下的曲径从不声张。
我是个易于在顺境和逆境中活下去的旅人,不需要太多的食物,更不需要美玉、丝绸、叮当当的金币、哀艳的花腔。
一个温凉适中的音符就足以把我打发掉,或者如弥天大雪中淡洌如水的老酒,藏起快意恩仇的寸断柔肠。
舞台旋转,灯光熄灭,站在黑暗中会更踏实更坦然。
我是长颈鹿,天生就没有声带,但是,可爱的女中音,口吐莲花,唱出:成熟!
我惊讶地发现,她唱出的,与我经历和想象的竟然毫无二至。
提线木偶
爬上最高的坡儿
然后,俯冲着
幸福地消失……
——《遗失的二胡曲》
不想过去和未来,只想这一天、这一刻、这一秒。灯光通透亦或昏暗,完全依赖于表达的需要。举手、投足、大幅度地张开嘴巴、笨拙地翻筋斗,这一切的动作和表情都不能自主。
是谁在暗中操纵着这个世界?
只想这一天、这一刻、这一秒,它们至关重要,亘古未有。
它们是美酒的最后一滴醇,是蜂蜜的最后一滴甜,是盐的最后一粒咸,是光线的最后一丝黯淡,它们在千钩一发的临界点完成质的蜕变。
谁曾经是我?
我曾经是谁?
是头戴瓜皮帽的少年,还是衣袂飘逸的飞天,是老狼还是小丑?是传说还是寓言?
调动所有的肌肉和神经,把每一场戏演完。
一场又一场,一天又一天,一生又一生,心里藏着一团温温吞吞的火,名字叫“忆念”。
散场。
一堆毫无价值的碎片瘫软在台角。
恰如我们无法言说的生活——波峰浪谷,幸福地堕落……
手掌中的坦途
揭开小小的疤——
铁钎通红,咝咝的烟雾中
那些繁盛之花隐秘之花
倒吸着凉气
——《我痴迷于嘀嗒之声》
生命线。事业线。爱情线。
全部命运已牢牢地握在自己的股掌之中!
而我是为数不多的反对者之一,像个能言善辨的小学生,目光清澈,举起手,举起昭然若揭的靶子。
我不怕回答错误,不怕哄堂大笑,不怕老师的愠怒,我什么也不怕,清清嗓子,洪亮地说:我喜欢平静安逸,也喜欢花天酒地;我喜欢知足常乐,也喜欢得陇望蜀;我喜欢天长地久,也喜欢喜新厌旧……
教室里笑声汪洋,老师用教鞭抽打着黑板,仿佛解恨似地抽打着我的黑衣。她恶狠狠的目光,前后紊乱的话语,宣告那节造句课彻底失败。
她气愤地对我们说:回家接着想——你到底“喜欢”什么?
然后声嘶力竭地宣布:下课!!
我不承认我有错,真的,我不是反对财富和占有,是反对占有财富的一些龌龊的手。
我的愚顽和坦诚设置小小的麻烦,但它们最后终究会搭救我!
我不说被挽留下来的淤泥浊水、残枝败叶,而倾向于从指缝间滤掉的流动。
不可挽回的神秘之音,请还时间以公正和自省。
三十岁的青春开始下山
太阳浴血而出的清晨
我终于幻化成浩繁中
刺伤你双目的
那个词
——《我是你没有说出的一个词》
山风穿过我的身体,慢慢地弱下去,我的身体弹痕累累,像莲子,过滤着流水和泥沙,抱紧蚌的秘密,高贵、笃诚。
我们坐在半山腰,坐在朱漆画廊的凉亭下,听波涛的蝉鸣,听泉,听松,享用着心灵的富有和安宁。
没有比脚步更长久的路程;没有比目光更高远的天空。
我们踌躇满志,指指点点,远处的微缩景观一一呈现:模具的村庄、丝绦的道路、波浪的山峰。
我们有少量的皱纹和华发,却沧桑着,讲一些各自难以忘怀的往事,虽然并不一定能使对方感动,但是每个人都在礼貌地倾听,并联想各自不同的生活,赋予公共情感以最广义的认同——先是一两声长叹;接着,叹息轻如微风;
最后,谁也不再出声,共同望着不确切的远山,目光迷蒙。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这山林多么空旷,多么幽静,却容不下四散荡漾的钟声,容不下一丝欲望的火星。
不知过了多久,其中的一个人轻声地说:我们下山吧。
时值正午,我们三十岁的青春开始下山……
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弄清,是我们中的哪一个最先觉醒。
油漆工的夏天
“我们不是像花儿那样,尽一
年的时光来爱;我们爱的时候……”
想不起花儿的开放,何况
一年的时光精确得不尽人情,有点荒唐
——《背景音乐》
当我省悟过来的时候,油漆工已几天不见,这多像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走远。
整整一个夏天,一批批油漆工在院子里漆着一批批的窗子。
整整一个夏天,我不仅仅嗅到油漆的味道,还嗅到海的腥咸。他们像一个个舵手,推动着一艘艘小小的船,小小的船航行在海天之间。
整整一个夏天,我的心情一片茫然,这与我们的相遇有着直接的联系。一年,还不算太久,而我却感到有一点孤单。我是先知,被自己的谶语应验。
不能返还。
我们内心的天空,往往需要别人帮助改变,是风雨、是雷霆、是万丈深渊,都由一双出奇不意的手涂涂抹抹、圈圈点点。樊篱虚设,围追阻截,心甘情愿的沉浸在所难免。
那一天,我推开窗子,企图推开那片滞重的海,却再也不见了熟悉的蔚蓝。
——荒唐的一定不是时间,而是我始终没记住油漆工什么时候离开了夏天。
鞋子的故事及其它
说与不说,做与不做
有许多事情该发生
迟早会发生,不必怀疑
——《草莓》
打开房门,玄关的地面上:
先是一双男人的鞋;
后来,是一双男人和一双女人的鞋;
后来,是一双男人和另一双女人的鞋;
再后来,还是一双男人的鞋。
这是一篇微型小说,这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
婚姻如鞋子,这比喻浅白、滥俗,毫无新意可言。但是,第一个说出真理的人,一定是被鞋子挤疼了脚,说不准还打过几个血泡。
经验的多米诺应声倒地,在最关键的部位拉响警报。
强光爆裂。夜的黑盒子分崩离析,四散成灰。
驿动。喊叫。哭号。
在新鲜的血腥中重又归于平寂。返回黑暗。
第一个说出真理的是英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一定是蠢才。
而实际上,我们都应该像庸才和蠢才一样活着——发生就任它发生,不发生又能如何?
我没日没夜地在纸上信手涂鸦,写一些疯话、傻话、狂话,就是为了等待着遭逢,并被那个克星的词硌一下,停顿、拌倒,也许从此再也爬不起来。
水的疫患
那个下午,我的心情
有不同的称谓
全是因为
这个复杂的世界
——《一个下午被泡在电话里》
从流水中抽出身子,同时也抽出花朵中的甜,抽出箭中的毒,难免有一点点难过和心酸。
我是个比较简单的复合体,约简到最小公倍数,却还有着数不清的不同侧面。这并不是我的最初想法,一个草履虫的处境是低等的,多少有点看不到前程的孤单。
不带包裹和牵挂,空着两手出游,以保留最敏锐的热爱和留恋,最简短的转身和弯转。
我像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没有时间停下来,没有时间睡觉,没有时间闭上双眼,让招摇撞骗的水草儿缠着,在一定的限度内发牢骚,散布些狂言。
我的时间哪去了,我的时间都被泡在水里了,像看不见的海绵只留下沉重、疲惫、密不透风的质感。
一个个下午排成队,等在门外,听到不同命名的叫喊爽快地应着,神情凝重地,再一个个被灰白的药水冲淡……
寂寞的自鸣琴
鲜润滴在泥土里,泥土深沉了几分
滴在空旷里,空旷苍凉了几分
我不说那常存的
只说流逝……
——《春天的雪注定站不住》
晚饭还不算太晚,剩余的时间可以游泳、散步或者谈天,我们绕过七转八弯的回廊、栈桥,有一搭无一搭地走走停停。
在台湾的最南端,在美丽迷人的垦丁,在夏都沙滩酒店,我有一个惊愕的发现——起初,我是被大堂里如泻的乐音所吸引的,后来,才看清了兀自起起落落的琴键——一台绅士般的钢琴,在大堂的一角无风自摇,无指自鸣!
一定是明眸皓齿的小妖精施了妖术,一定是身着隐身衣的魔女穿着透明的水晶鞋在不停地旋舞,不停地模拟着往事、前尘、风云和涛声。
妖言惑众。
高贵的妖。典雅的魔。埋伏下陷阱,暗处好机关,单等一个意志薄弱者自投罗网,乖乖地服刑。
揪心。泪珠儿在眼角儿等着,一个音符就能碰落,溅起漩涡。我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悲痛足以把太平洋填平。
我望向窗外,碧波的海水蓝得愁人,模糊不清……空空的沙滩上,有几个游人在嬉戏、走动……
磁卡电话接通了乡音,接通了遥远的问候。
妈妈说:米兰起死回生了!米兰开花了!满屋清新……
当我在午后绵密的秋雨中想起这一切,那个日子离开我已足足一千天。沙滩上的游人还在走动吗?米兰早已香消玉殒。一千天,远得近在眼前,近得远在天边,而自鸣琴的寂寞,如今谁人倾听?
时空隧道
在人群中沉默下来
是一棵树的品质
在树中沉默下来
却是一个人的奢望
——《许多树团结地站在一起》
从众多的寂寞中,我挑选最轻的一个,让它像氢气球一样飘着,在体内游荡,窜出绿色的火苗,跳跃着,守成着,模拟一棵树的境遇:出生、成长、死亡,粗壮着腰身,闷声闷气地压住秋天的韵脚。
一列火车穿境而过,有几分钟的茫然若失,但是很快,就若无其事地蜿蜒而过,冒着烟,喘着气,像一个人一样在大地上出没。
如果能够停下来多好,像神明举着永昼的火把,或者像一场社戏迟迟不肯平熄噼噼叭叭的篝火。
命若琴弦。
收留几多空谷绝唱?
围着炉火饮酒、品茶,悠悠地说话,看慵懒的雪花把碎石甬道埋没,顺便埋没掉还没有干枯的青草和花朵。
你双手支着下颌,望向窗外的眼神有圣母的安详和光辉,却在喧哗的穿越中深陷泥淖,隐不住焦灼。
这一次旅行没有目的
晚祈。安睡的理由是否更加充分
最好是初秋,还不算太萧条
你摘掉黑礼帽,没有一丝阴影,天空
蓝得郁闷、呆板
漫漫苦役。“死亡消磨着我,永不停息。”
——《记忆(四)》
旁逸斜出的枝丫太多,它们靠吸食我的膏脂存活,一天天伸展腰肢,生长、衰老、触摸阳光。但是,这欢快的寄居令我不得轻松,我必须在仓促间打理好那些沉重的异香。
我是根系繁茂的树种,与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不能走远,充其量,每一次旅行都是迫不得已。
秘而不宣的夜晚,我早早地睡去,在假死的状态中把自己消磨,并用另一种柔软的方式,与白昼里的另一个自己和解。
早早地睡去,是为了早早地醒来,在骚动而安谧的晨曦中,孤芳自赏,再麻木不仁地继续操练,神清气爽地在喧嚣中失语。我有融入的权力,但是更有保留的权力,有格格不入的必要的自由。
出去走走,这一次旅行没有目的——遇到黄昏就支起帐篷,遇到阳光就打开花蕾,遇到不讨厌的人就简短地说说话。也许,再喝一杯淡淡清茶。
一切皆是自然,自然得就像这一个人生,没有一点预见。
通联:124010 辽宁省盘锦市作家协会 宋晓杰
转载于中国散文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