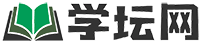昌耀作品选
2021-08-10 05:46:39 33
昌耀,原名王昌耀,1936年6月27日出生于湖南常德桃源,九三学社会员,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文工队队员,河北省某军校学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调青海省文联任创作员,参加创办文学杂志《青海湖》,并担任编辑工作。1957年因创作《林中试笛》短诗二首,被诬“反党毒草”打成右派。1959年被流放到祁连山深处的劳改农场,在这里度过了20年痛苦而漫长的岁月。1979年沉冤得以昭雪,回到《青海湖》编辑部。八十年代以后作品引起广泛注意。2000年2月,中国诗歌学会授予昌耀首届“厦新杯”诗人奖。2000年3月23日,昌耀与肺腺癌抗争数月之后,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从青海省人民医院堕楼而下,实践了回归母亲怀抱的愿望。
昌耀出版的作品集有《昌耀抒情诗集》、《情感历程》、《噩的结构》、《命运之书》、《昌耀的诗》、《昌耀诗文总集》。昌耀的作品有清新鲜活的现实写照,亦有浪漫主义类似惠特曼式的激情奔放的呐喊。但更多如《空城堡》那洋,用近乎现实主义手法抒写自己的心灵世界。其诗作想象的奇峻、语言崎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诗的总体风格表现为冷冽、凝重与热烈、奇峻的和谐统一。昌耀是生活在精神西部的圣徒,是二十世纪后期活跃在诗坛的优秀诗人。诗人祝勇在《昌耀不死》中写道:“白昼里他是狂沙埋不了的高贵,月色里他是鹰隼一样游弋不休的伤感,”他“像一只敏感的苍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滑翔轨迹,全然不去理会外面世界的脉息。不管怎么说,昌耀都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诗人韩作荣著文称昌耀为“诗人中的诗人”,“他的作品即使和世界上一流诗人相比,也不逊色”
烘 烤
烘烤啊,烘烤啊,水杯的内热如同地火。
毛发成把脱落,烘烤如同飞蝗争食,
加速吞噬诗人贫瘠的脂肪层。
他觉着自己只剩下一张皮。
这是承受酷刑。
诗人,这个社会的怪物、孤儿浪子、单恋的情人,
总是梦想着温情脉脉的纱幕净化一切污秽,
因自作多情的感动常常流下滚烫的泪水。
我见他追寻黄帝的舟车,
前倾的身子愈益弯曲了,思考着烘烤的意义。
烘烤啊,大地幽冥无光,诗人在远去的夜
或已熄灭。而烘烤将会继续。
烘烤啊,我正感染到这种无奈。
致修篁
篁:我从来不曾这么爱,
所以你才觉得这爱使你活得很累么?
所以你才称狮子的爱情原也很美么?
我亦劳乏,感受严峻,别有隐痛,
但若失去你的爱我将重归粗俗。
我百创一身,幽幽目光牧歌般忧郁,
将你几番淋透。你已不胜寒。
你以温心为我抚平眉结了,
告诉我亲吻可以美容。
我复坐起,大地灯火澎湃,恍若蜡炬祭仪,
恍若我俩就是受祭的主体,
私心觉着僭领了一份祭仪的肃穆。
是的,也许我会宁静地走向寂灭,
如若死亡选择才是我最后可获的慰藉。
爱,是闾巷两端相望默契的窗牖,田园般真纯,
当一方示意无心解语,期待也是徒劳。
我已有了诸多不安,惧现沙漠的死城。
因此我为你解开发辫周身拥抱你,
如同强挽着一头会随时飞遁的神鸟,
而用我多汁的注目礼向着你深湖似的眼窝倾泻,
直到要漫过岁月久远之后斜阳的美丽。
你啊,篁:既知前途尚多大泽深谷,
为何我们又要匆匆急于相识?
从此我忧喜无常,为你变得如此憔悴而玩劣。
啊,原谅我欲以爱心将你裹挟了:是这样的暴君。
仅只是这样的暴君。
鹰·雪·牧人
鹰,鼓着铅色的风
从冰山的峰顶起飞,
寒冷
自翼鼓上抖落。
在灰白的雾霭
飞鹰消失,
大草原上裸臂的牧人
横身探出马刀,
品尝了初雪的滋味。
斯 人
静极——谁的叹嘘?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援而走。
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
一片芳草
我们商定不触痛往事,
只作寒暄。只赏芳草。
因此其余都是遗迹。
时光不再变作花粉。
飞蛾不必点燃烛泪。
无需阳光寻度。
尚有饿马摇铃。
属于即刻
唯是一片芳草无穷碧。
其余都是故道。
其余都是乡井。
人·花与黑陶砂罐
1
一束从废园采来的杏花(其间杂陈的白色碎朵据
称是夜来香)在妻的拈握中迟疑了许久:
窗台上实无可落脚的地方了。
2
让她们生长在各自的枝干上原不好吗?
何必让她们痛苦?
何必让她们绝望、孤独、饥渴、涕零?
妻说:你别管。
3
窗台,那陶罐被一束鲜花罩住深不可测的渊口。
我见不到渊底的一潭寒水了......
听不到渊底欸乃一声的舟橹了......
嗅不到神农氏从渊底袅袅升起的草药香......
世事总是出人意料。
总要为人生妒?......
良 宵
放逐的诗人啊
这良宵是属于你的吗?
这新嫁忍受的柔情蜜意的夜是属于你的吗?
不,今夜没有月光,没有花朵,也没有天鹅,
我的手指染着细雨和青草气息,
但即使是这样的雨夜也完全是属于你的吗?
是的,全部属于我。
但不要以为我的爱情已生满菌斑,
我从空气摄取养料,经由阳光提取钙质,
我的须髭如同箭毛,
而我的爱情却如夜色一样羞涩。
啊,你自夜中与我对语的朋友
请递给我十指纤纤的你的素手。
热苞谷
手持热苞谷的一对小男孩在街头追戏。
手持的热苞谷如同奥林匹亚圣火接力的火炬。
一切在加快成熟。
请看街头一对追戏的小男孩
他们手持鲜嫩的热苞谷大步越过一片一片太阳
像越过一片一片湖水。
像越过母亲的弹簧床。
他们躲过行道树忘情地朝前方追戏。
他们嬉笑什么?
林荫道上奔跑着男孩子蓝蓝的背心。
和高尔夫呢西服短裤。
和雪白的运动鞋。
父母在一旁骑着自行车随后尾随。
父母在一旁骑着自行车随后尾随。
奔跑着的一个男孩子
忍不住停步掰开热苞谷的一叶苞衣。
喜气的谷粒透过丝絮射出迷人的十字星辉
男孩子更紧地追逐另一个奔跑的男孩子。
热苞谷金黄的子实让城市的夏季瞬刻成熟。
男孩子奔跑在铁桥。奔跑在河岸。奔跑在光栅。
他们呼唤什么?
他们嬉笑什么?
听得到热苞谷飒飒的风声。
一切请加快成熟。
大街的看守
无穷的泡沫,夜的泡沫,夜的过滤器。
半失眠者介于健康与不净之间,
在梦的泡沫中浮沉,梦出梦入。
街边的半失眠者顺理成章地成了大街的看守。
寡淡乏味,醉鬼们的歌喉
撕扯着人心,谁能对他们说教仁爱礼义?
一会儿是夜归人狠揍一扇铁门。
唢呐终于吹得天花乱坠,陪送灵车赶往西天。
安寝的婴儿躺卧在摇篮回味前世的欢乐。
只有半失眠者最为不幸,他的噩梦
通通是其永劫回归的人生。
但黎明已像清澈的溪流贯注其间,
摇滚的幽蓝像钢材的镀层真实可信,
一切的魑魅魍魉暂时不复困扰。
乡 愁
他忧愁了。
他思念自己的快谷。
那里,紧贴着断崖的裸岩,
他的牦牛悠闲地舔食
雪线下的青草。
而在草滩,
他的一只马驹正扬起四蹄,
徵开河湾的浅水
向着对岸的母畜奔去,
慌张而又娇嗔地咴咴……。
那里的太阳是浓重的釉彩。
那里的空气被冰雪滤过,
混合着刺人感官的奶油、草叶
与酵母的芳香……
——我不就是那个
在街灯下思乡的牧人,
梦游与我共命运的土地?
生 命
我记得。
我记得生命
有过非常的恐惧——
那一瞬,大海冻结了。
在大海冻结的那一瞬
无数波涌凝作兀立的山岩,
小船深深沉落于涡流的洼底。
从石化的舱房
眼里石化的大海只剩一片荒凉
梦中的我
曾有非常的恐惧。
其实,我们本来就不必怀疑,
自然界原有无可摧毁的生机。
你瞧那位对着秋日
吹送蒲公英绒羽的
小公主
依然是那么淘气,
那么美丽!
立在河流
立在河流
我们沐浴以手指交互抚摸
犹如绿色草原交颈默立的马群
以唇齿为对方梳整肩领长鬣
不要耽心花朵颓败:
在无惑的本真
父与子的肌体同等润泽,
茉莉花环有母女一式丰腴的
项颈佩戴。
立在河流我们沐浴以手指交互抚摸。
这语言真挚如诗,失去年龄。
我们交互戴好头盔。
我们交互穿好蟒纹服。
我们重新上路。
请从腰臀曲直识别我们的性属。
前面还有好流水。
朝朝暮暮
我承认,从那以后眼睛就易于潮湿。是性格懦弱?不辩解了。但我愿提及铁凝近作里的一段情节,讲到一个少年打靶的梦想就要成为现实,忽被从操场叫到学校食堂,面对山一样堆积而需他一一剔除腐叶的白菜,仅因其家族有“革命营垒的对立面”,孩子对步枪怀有的那种敬畏的迷恋也就剥夺净尽。那少年坐下来强忍住眼泪劈菜帮。四周静寂得很,他终于听见“泪珠落在菜帮上的噗噗声”,竟是一种嘹亮。后来冻疮生满双手。是懦弱还是坚强?铁凝称他是最坚强的男子。